据悉,10月28日—10月29日,在两天之内,西南大学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所长黄其洪教授应邀先后在东北师范大学哲学院、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和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做了三场学术报告。这三个机构都是学术重镇,都是A级学科所在地,能够在这三个地方连续做学术报告,至少可以说明学术界同行对西南大学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所研究工作的高度认可,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黄其洪教授研究的前沿性和学术影响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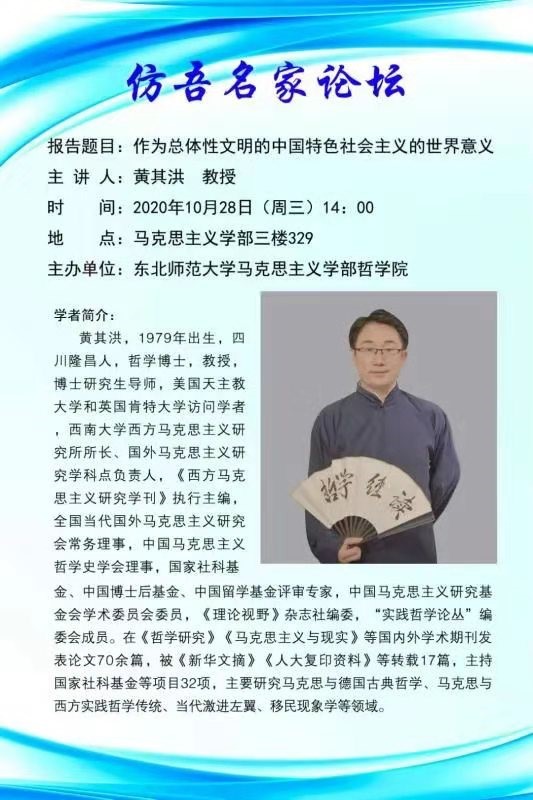
10月28日下午2点开始,黄其洪教授在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部三楼329报告厅作题为《作为总体性文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世界意义》的学术报告。东北师范大学哲学部魏书胜教授、程彪教授、陈士聪副教授、马军海副教授等老师和东北师范大学近两百人听取了此次讲座。在讲座中,黄其洪教授强调,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在生产力层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出现了新的要素和革命性变革,在生产关系层面的创新已经使中国与西方形成了原则性的区别,在政治上层建筑层面已经显现出比西方自由民主制度更高的活力,在意识形态上层建筑层面也展现出与西方现代性之间的原则性区分。虽然直到目前为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这四个层面还存在着许多具体环节之间的不适应和不协调,发展还存在着不平衡、不充分之处,还需要不断推进改革,但是,从总体上看,四个层面相互之间在基本原则方面是相互适应和相互推动的,正在走向成熟和定型,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成为一种新的总体性文明。与此同时,西方现代性却不断地显示出它自身的限度,在西方文化的范围内,找不到克服这种限度的方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新的总体性文明刚好为在全世界范围内超越西方现代性提供了重要的资源和可能性,不仅对于中国、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具有重要的意义,对于西方国家也具有新文明定向的作用。围绕着“如何判断一个社会体系是否是一个总体性文明的标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否已经是一个总体性文明”“西方现代性的基本特征”“西方现代性是否已经走向了自身的限度”“中国特色会主义是否已经超越了西方现代性的限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具有的可能的世界意义”等问题,黄其洪教授做出了深入浅出、生动活泼的阐释,整个讲座大约持续2个小时。虽然,那一天黄其洪教授的身体状态不是太好,但是,整个讲座的效果还算可以。

10月28日晚上7点钟开始,黄其洪教授又来到吉林大学南湖校区一教三阶,作题为《论马克思与海德格尔在历史性问题上的差异》的学术报告。黄其洪教授在报告中首先介绍了马克思和海德格尔在何种意义上可以在历史性问题上进行对话,马克思的历史性思想指的是什么,有什么特点,海德格尔的历史性思想又指的是什么,二者有什么共同点。然后在此基础上,重点分析了二者之间的差异,强调了二者三个方面的差异,即个体的历史性与群体的历史性的差异、形式的历史性与实质的历史性的差异、领会的历史性与实践的历史性的差异。黄其洪教授强调,如果忽视了这种差异,完全以海德格尔来解读马克思,会造成一系列的理论后果,当代西方激进左翼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受到了这种思潮的影响,从而造成了无法找到革命主体、无法找到现实的革命道路等理论困惑。通过此次讲座,黄其洪教授一方面强调马克思和海德格尔之间确实在历史性问题上有相似之处,可以相互对话;另一方面又强调不能将二者完全等同起来,提醒大家“以海解马”必须意识到自身的限度。报告内容本身是很艰涩的,但是,黄其洪却能深入浅出地传达这些艰涩的思想,使与会的听众能够茅塞顿开,收获满满。讲座在经久不息的掌声中结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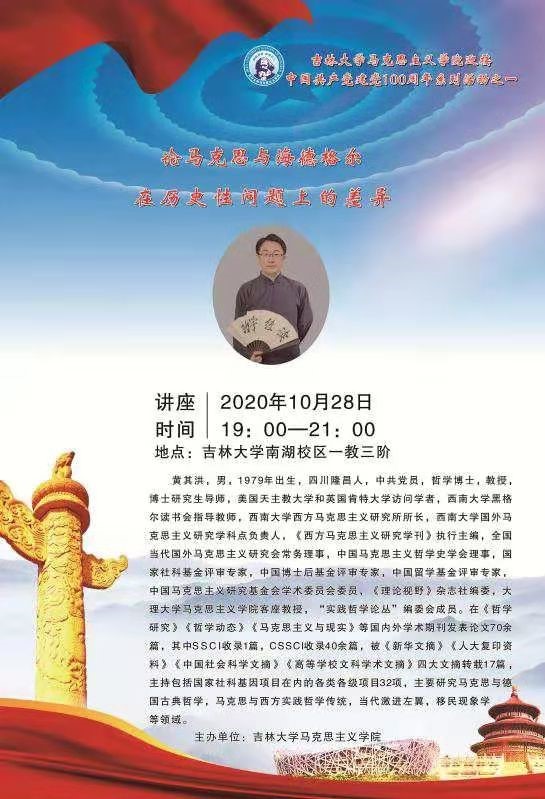
10月29日晚上6点半,黄其洪教授来到吉林大学中心校区东荣大厦A904会议室,为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的师生作了一场题为《移民现象学兴起的背景、核心问题和理论定位》的学术报告。这是黄其洪教授第一次回到母校母院做学术报告,他的心情还是很激动,他把此次讲座当成了向母校母系恩师的一次学术汇报。移民现象学是黄其洪教授近五年来开创的一个学术分支,他的研究代表这个领域的学术前沿,他在自己的母系讲这个题目,确实是想以这种方式向母校的恩师、前辈致敬。吉林大学哲学学科的两位青年长江学者王庆丰教授和白刚教授到现场听取了报告,并参与了现场讨论和点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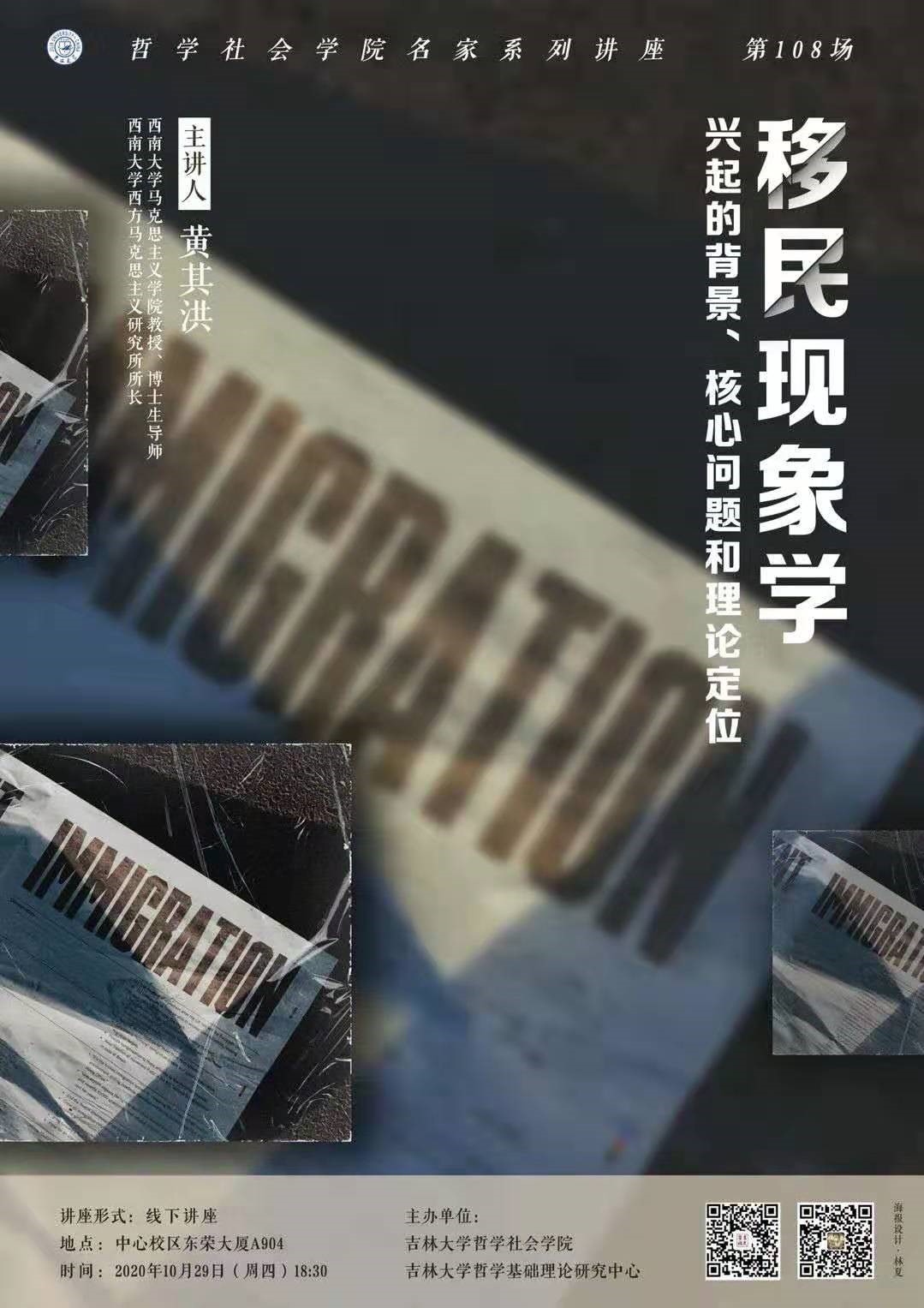
在报告中,黄其洪教授强调,移民现象学是在美国和欧洲近年才兴起的一门应用现象学分支,它的兴起既与西方哲学进入现代以来的拒斥形而上学的传统有关,也与现象学的不断具体化和深化有关,还与90年代以来极度不平衡的全球化所带来的文化冲突、宗教冲突和政治动荡以及大量中东、西亚和北非难民涌入欧洲和美国有关。移民现象学是以现象学的方式去研究移民问题,它主要有三个问题群:有关新移民的自我意识重构问题、有关原住民的自我意识重构问题和有关新的社会契约的形成和认同的意识基础问题。这其中的每一个问题都是一个庞大的问题群,都由许多具体的问题构成,这些问题环环相扣,构成三个相对独立的系列。在这些问题中只有一小部分问题已经得到较好地解决,其他绝大部分问题还是全新的,等待哲学家们去开垦和耕耘。中国的哲学家在这一领域基本上和西方是同步的,我们完全有可能开创有中国特色的移民现象学学派,为世界性的移民问题提供中国方案。为了中国学界能够迅速准确地把握移民现象学的理论特征,不至于在学习和研究过程中发生方向性的错误,有必要对移民现象学进行准确的理论定位。对于定位移民现象学来说,有三组定位是很关键的:在移民现象学中存在着一种存在设定,即文化异质性设定,因而它是对特殊形式的空间和感性材料的意识分析,所以移民现象学属于应用现象学,而不是纯粹现象学;在移民现象学三个不同向度的反思中,意识反思的活动和意向对象都具有经验性,都是暂时的,局部的,不是一次性完结的,其最后的目的在于实现文化他者之间的和谐关系,这种和谐关系不能只停留在理论和意识内部,必须深入到意志和情绪的领域,因而它要达致实践的领域,所以移民现象学属于实践哲学而不是理论哲学;移民现象学已经不再停留于主体性的领域,也不再停留于一般的主体间的领域,而是深入到文化间性领域,是一种关于文化间性的意识反思。
(西南大学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所 供稿)

